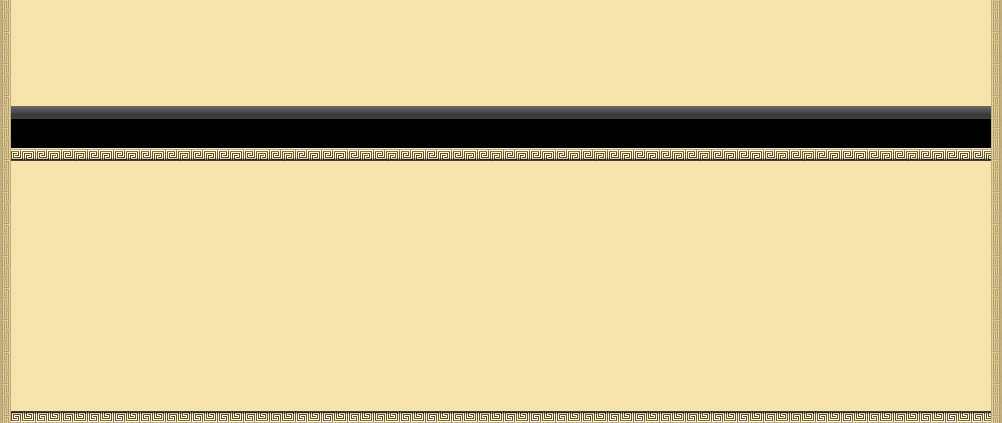已經打了四個七,你們的工夫當然有了深入處。第一個七不知用功,第二個七知道用功,第三個七工夫就用上了,第四個七當然會有深入。在此起七中忙了一些人:堂裏的班首師傅時時刻刻照應你們,講話多了,恐怕你們動念頭;减了又减,深怕多講一句,動師傅們的念頭。講開示、公案、典章,不帶一句經典、語錄;乃至外面任何境况,都不與你們講一句。為甚麼呢?因為你們參的是“念佛是誰”,其他一切言句都不合這一法,這是他們的苦心。及至看見你們這裏也不對,那裏也不對,心裏挨不過,要説,要講;説出來,又怕師傅們動念,衹好自己放下來,此亦復是成就師傅們的道念。維那師傅堂裏、堂外的照應,乃至跑香長,深怕師傅們傷氣;跑短,又怕師傅們精神不足,坐起香來容易睡覺;催起香來,深怕打著師傅們的耳朵,或打傷了退師傅們的道心。一天到晚在你們身上用心,一副精神完全用在你們身上。一切監香師、香燈師、司水、悦衆,內、外護七,外寮、庫房、客堂,都是為你們用功辦道,成就你們打七。今天打了四個七,還説工夫没有深入!考工的規矩與上次同,一考就要答。但是,答出來要天搖、地動;不然,不是火葬,就是水埋。交代在先!(考工、解七從略。)
十一月十五日開示(伍七第二日)
前四個七的講話,都是教你們用功。最初是不知道用功做甚麼?又不曉得甚麼叫做用功;漸漸知道要用功,又不曉得怎麼用法,從甚麼地方下手。再則,初初的知道一個“念佛是誰”,又不深信,這都是你們過去的程序。所以一向講的為甚麼要用功。但工夫下手的路途,岔路多得很,故此要領你們走這一條正路;路上的荊棘又替你們打掃得光光的,這條路教你們走,不教有一點障礙;一層一層的説給你們聽。今天四個七打下來,你們不知道也知道,不用功也要用功,不肯向這條路上走的人,也向這條路來了;大家都上了路,不能再説未上路的話,要替你們講講工夫話了。但在你們當中還有好幾位,連“念佛是誰”尚没有相信,怎麼參,怎麼起疑情?一回也没有做一下子;人家跑,你也跟到跑跑;人家坐,你也跟到坐;根本没有動一腳,那裏説得上已經走上了正路的話?若要以你們這個樣子看,工夫話還要説嗎?説,還有甚麼用呢?本來是没有口開,而又不能不講,大概有一二位又需要我講工夫程度的;即使一個人也没有,我又不能因没有而不講。你們以為我没得口開,是你們工夫用到了没口開的地方;你們真用到没得口開的地方,我走三個空圈子,我是不言之言,你是不聽之聽:不言之言,是真言;不聽之聽,是真聽;那是很好的!恐怕不是這個没得口開罷!是因為你們工夫的程度一點也没有。可能我講的話在前,你們就跟我的話行在後;譬如行路,我在前一里路,你在後一里路,你也看到我,我也看到你,這樣纔對。今天,光得我在前頭講,你在後頭行不上,我到講了十里八里下去,你一里路還没有走;你也看不到我,我也看不到你;我講向南,你到向北,還能對嗎?我的話講來,還能言、行相應嗎?既不能相應,不是不要開口嗎?我是這樣没得口開,並不是工夫上没得口開。或者有人説:“你這樣講,恐怕委屈人。”也許你委屈人;但是,寧可以我委屈你,是很好的,恐怕不委屈。你以為:“你哪裏知道人家心裏的事?”雖然你的心在你肚子裏,你的人站在這裏,我把你一看,望到對過清清爽爽的,如一個琉璃瓶一樣,裏頭心、肝、五臟,看到一點也不差,你心上的事,我還看不到?我還委屈你嗎?宗門下的事,不是説説就了,也不是付於來日的。教下開座講經,可以下座睡睡覺,外面跑一跑;因為今天講過,就付於來日。宗門下不是:要今天説的今天行,明日説的明日行;我説的,就是你們行的;你們行的,也就是我説;言、行要相應;倘若言、行不相應,不是宗門事。你們有不少的人,未進禪堂以前,以為禪堂了不起,十方諸佛、菩薩、諸祖師出身之所;禪宗一法,極玄而妙,是很相信。今天住到禪堂,反過頭來“不好了!外面説禪堂怎麼好,而今進堂以來,七也打過三四個,没有甚麼了不得,不過就是這樣子罷!在外面聽到人家的話,恐怕是人家騙我的!我到要想過旁的事幹幹纔好!”你們這一種人,可憐,可憫!真是不可説!我亦要替你們把這一種病源指出來,使你們知道是病,可以向前走走。這一種人,“念佛是誰”影子也没有,我問你“念佛是誰”,你還有點影子嗎?不但没有,還以為:“不好了!我所學來的,會到來的,很多很多的,以前提一個題,似乎涌涌的言句就可以説出來。今天,把禪堂一住,七一打,反過來,文章想不起,一句也想不出來,一想,再想,終歸想不起;好像肚子裏空了,似乎不相應,七不能再打了!再打,恐怕將我費了許多辛苦學得來的《楞嚴》、《法華》都忘去了!恐怕空費許多的經濟,空費多少困苦;這樣子,七不願意打了!把肚子打得空空的!”你還是這一種心理。我説:你們不要弄錯了!這是好事,不是壞事。你們還相信嗎?我説:你們學到來的忘掉,會到來的忘掉,不算事;還要你們連學的是甚麼人還要忘掉!連會的是甚麼人也要忘掉!你們大家領會一下子,還要深一層,把我問你們學來的忘掉,學的人忘掉了没有?可憐,可憐!學到來的還是滿滿一肚,哪裏肯把它忘了!天天坐下來,還要摸索摸索,深怕忘了;學的人忘掉,哪裏説得上!宗門下,首先要你空,要你忘!空了,忘了,那個時候,我自然會再與你商量。你為甚麼不肯空?不肯忘?世界上甚麼事都要講求進步,就是你們學教,亦復要進步;你們今天住禪堂,為生死大事,求成佛、作祖的,為甚麼不講進步?學來的,會來的,少許忘了一點,還不願意,你們自己想想:可憐不可憐?所以要你們大家認識。能把我能學、所學忘得光光的,這是好事;不忘,還要勇猛忘了纔是。那麼,你不用功的人,光打七覺得很好的,坐坐,跑跑,睡就睡,一下子倒也不怕,很受用。用功的人,反過來,倒是五心煩躁,身心不安。為甚麼呢?因為,用功的人,他知道生死非了不可;我的生死是苦,大地衆生的生死更苦;若要令他們離苦,必須我先離苦,而後再度他們的苦。我要離苦,非用功不可;我要度衆生離苦,亦非用功不可。所以一天到晚,刻刻用功,時時研究工夫,深怕工夫打失,總要工夫成片;因不得成片,總是自己剋責自己;因為大事未明,是這樣的不安。但是,你們大家在這裏還有一半人是這樣?或者三份之一是這樣?恐怕也没有!假使有一個兩個,也是好的!還算是一個道場!若要一個也没有,這一句話是怎麼講法?教我開口講話,還有味道嗎?你們想想看!我看你們都不是這樣,是甚麼樣呢?“常住上真是向我們要命!八個七打了就罷了!為甚麼又添兩個七?這不是與我們為難嗎?還説得好聽,成就我們!真實不要你成就,早點解七罷!讓我們睡睡覺,休息休息;似乎現在去睡纔好!”哪裏還有精進、勇猛的一句話!想快活快活,適意適意,纔對呢!對嗎?你們自己想想看:這樣,還是一個辦道的人嗎?師傅們!要認真吃一番苦,這樣快活、適意,不能算事的;還得把“念佛是誰”提起來,參去,纔有受用。參!
十一月十六日開示(伍七第三日)
“一念不覺生三細,境緣纔動成六粗。”宗門下的事,不講根、塵、五識,六、七、八識,一概不講;衹講粗、細。對於“念佛是誰”當然要講:因為這一法是發明我們本有的一法。雖然,它可以發明本有,不説也不能使人行這一法。或者有人説:“既然有説、有講,莫非是教宗嗎?因為有言、有説。”你們會錯了!宗門下所講所説,不與教同,亦不與宗同;反過來,也與教同,亦與宗同,與佛同,與祖同,一同一切同。今天與你們講粗;本來,宗門下細亦不可得,説甚麼粗?實在是方便之方便,替你們中下根的人,不得不講;上根利智的人,是一超直入,不假説粗説細。甚麼是中下根的人?因為與上根的人稍次一點,故此説是中下根人;恐怕還是與你們客氣。何以呢?這個粗,你們還知道嗎?是個甚麼東西?是大、是小?是圓、是方?你還曉得嗎?你們能曉得,出來告訴我!你們有這麼一個人,我就許你是一個中下根的人;恐怕你們没有一個人知道,連這一個粗的影子都不曉得,哪裏還説得上是中下根人?下下根人還是勉強;説是中下根人,是客氣罷!那麼,究竟這個粗,還是個甚麼樣子?有多大呢?恐怕還不容易知道;我就告訴你們,恐怕也不容易曉得。略説一點你們聽聽:你們今天用功用不上是粗,不相信用功亦是粗;不信“念佛是誰”是粗,疑情發不起亦是粗;怕吃苦是粗,要快活亦是粗。你説它有多大呢?有情,最大是金翅鳥,還没有它大!無情,大山、大海,亦没有它大!它既然有這麼大,為甚麼不見呢?因為我們整個的在粗裏頭。譬如:杲日當空,雖然有白雲遮蓋,還有少份光明;假使一陣黑雲整個的蓋起來,便伸手不見掌。假使有一個人,一輩子都是在這黑地方過日子,一腳泥巴,一腳狗屎,問到他:“腳下是泥巴麼?”他説:“是的。”再問他:“還有狗屎没有?”他説:“没有,是泥巴。”狗屎當泥巴踏在腳下是不知道;究竟問他泥巴是甚麼樣,他到没得口開。何以呢?向來没有看到過,哪裏會知道是甚麼呢?就等於我們這一件事,如:杲日當空,因為被業障一遮,就似一點雲霧;今天也造業,明天也是造業,久久的,就如黑雲一樣,把一個本來的光明,遮得牢牢的。今天問到你:“粗是甚麼東西?”没得口開,因為没有見過,哪裏會知道!就如黑地裏見泥巴一樣。你們想想:被這一個粗障,把你們本有的光明障得氣也不透。今天住在這裏頭,還以為:“好得很!”一向你都住在障裏頭,連這一個障都不曉得,哪裏説粗不粗!粗裏、粗外這句話,還安得上嗎?今天,教你們:天下的事不要相信,要相信一個自己;你們為甚麼不相信自己?是被粗障障住了!任何法門不要你相信,“念佛是誰”這一法要你們相信,你還是不肯相信,何以呢?亦是粗障障住了!你們若有一個人有點向上的知識,一個了生死的堅决心,説:“天下人被它障住可以,我是不能被它障的;若我被它障住,我還算一個人嗎?”自己與自己商量計劃,並不是甚麼奇特事,又不是甚麼難事;就是不相信自己,不相信“念佛是誰”。今天,我非相信不可,任你障得最牢,我總要打破你;没有其他,衹要相信“念佛是誰”,就能打破障。被它障住了,就是不相信;不被障,就會相信;這是很顯明的。我這麼一講,你們有心於道的人,當然有個領會處。我説:你們不相信“念佛是誰”,你就把“念佛是誰”相信一下子,提起來參一參;等到你知道一點味道,恐怕就不同了!何以呢?你若把“念佛是誰”參一下子,不明白,就在這裏追究:是哪個?到底是誰?咦!似乎有個東西,大概就是我自己罷!再一參究,不錯!是我自己!雖然不十分相信,終歸被我見到一點;就如昊日當空黑雲遮住,忽然黑雲退了,還有點白雲遮住一樣。那麼,白雲遮日,總還有點看到;我們的本來面目被障遮蓋滿了,今天把障少許去一點,當然要看到一點;不十分清爽,就如一點白雲相似。自己見到以後,那是很好的;無量劫來没有見到,你今天把“我”見到了!我再問你:“相信‘念佛是誰’嗎?”你一定説:“不相信;我見到自己就罷了!還要相信‘念佛是誰’做甚麼?”你倒又錯了!你見到你自己,怎麼會見到的呢?你要曉得:“念佛是誰”很吃了一番苦,今天也是磨,明天也是擦;你的自己,是“念佛是誰”苦中得來的。你若不相信它,不是忘了本嗎?你們想想:對不對?可見到“念佛是誰”是去我們粗障的一法,是明我們本來面目的一法。若要發明本有,了生脱死,非“念佛是誰”不可。各人發起心來──參!
十一月十七日開示(伍七第四日)
生前的事,各人都知道,都相信;生後的事,甚麼人都不知道,不相信。因為生前的事,都親自眼見,不能不相信;生後的事,因為未見到,所以不相信。你們以為:“這個肉殼子的我,是很好的,非要愛惜它、非要寶貴它不可!將來有七八十年的受用。”這是你們最相信。“生後的事,我又没有見到,你教我相信個甚麼?”大概人人都是這一個知見。你們以為七八十年是很長的。你要曉得:生後的果報,與你七八十年的長比較,生後一彈指的功夫,就有你七八十年長。你還相信嗎?還説一天、一月、一年?他過一天,我們要過幾大劫!考究到這一點,我來比較一下子,可算這七八十年的功夫,似石火電光的一瞬間。但那一個長期裏頭的生活,就是在我們這個石火電光中造成的;造的甚麼生活,就問我們現前這一念是個甚麼念頭。念頭固然多得很,我們不要講多,就説一個念頭罷!這一念感甚麼果?古人云:“毫釐繫念,三途業因。”三途是甚麼?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你們想想,一毫釐的念頭,就要招這麼大的報,還要説一天到晚打妄想、翻業識?這樣的感果,我真不要講!次則,你們想過七八十年,閻王老子他還不由你,他一叫你去,你趕快跑,一刻也不能遲;就等於一根繩子這頭拴在你鼻子上,那頭就在閻王手裏;他把繩子一拉,你就跑。這是没得客氣的,恐怕比我們拉牛還要厲害十倍!他把你拉去,叫你變牛,就去變牛,馬上牛皮就到身上來了,角就安在頭上了,尾巴也安上了;你還有多大的本事把牛皮、牛角去掉?恐怕不由你!叫你去,你就去,少停一刻不行;要想不去,更做不到。可憐!我們那個時候,吃苦不能由己。那麼,變牛一次還不算了,恐怕變了一個又一個,骨頭堆起如山一樣,牛形脱後,纔可换一個其他東西去變變;他的期限很長很長的,不是我説來嚇你們的!在過去,有一位老比丘誦《金剛經》,念的音聲不好聽;這位老比丘已證四果,年老音聲當然不好聽,有一位年輕比丘在旁説:“你誦經的音聲,好像狗子吠聲一樣。”老比丘當下就説:“你講這一句話,你將來不得了!墮了地獄,還要去變狗子。”那位年輕比丘聽了,大吃一驚,趕快求懺悔,痛哭得不得了。老比丘説:“你有這樣的懺悔,地獄可免;狗子身不可免。”過七日後,年輕比丘死了,閻王老子叫他變狗子去;他還問閻王:“我為甚麼變狗子?”這一句話還未問了,狗子的皮和尾巴早已安好;後來,變狗一個一個的骨頭,堆起來,有須彌山那麼高大。你們想想:這一句話的果報,有這麼厲害!這不是我説的,是古人典章證明的,你們不能不信。你們大家想想:閻王老子這一根繩子拴在我們鼻子上,還厲害嗎?任你有天大的本事,還能逃得了嗎?你們真要逃避他,决定不到閻王老子那裏去,也不算一回事;要不去,就可以不去!極容易的事,恐怕你們又有一點不相信:“閻王老子那麼厲害,翻天的本事,也逃不了他的手;你還説容易,不算一回事,我那裏相信?”我要説個鐵證你們聽聽,就知道了:以前,有個金璧峰,他的本事好得很,夏天到清凉山過夏,冬天到南方來過冬,很好的。有一天,閻王叫小鬼來拴他,費了許多工夫纔把他抓住;他是有本事的人,就問小鬼:“你捉我做甚麼?”小鬼説:“閻王老子叫我來捉你的。”他説:“你還能慈悲、慈悲,讓我七天?你再來,我跟你去。”小鬼説:“不行!”再三懇求,小鬼也有慈悲,説:“好!容你七日可以,你去!我七天再來。”他見小鬼去了,他就把“念佛是誰”一提,拳頭一捏,牙關一咬,“究竟是誰?”“到底是誰?”這一來,拼命也不放鬆。到第七天,小鬼來了,甚麼地方都找過,天上、人間,虚空裏、虚空外,都找過,也找不到。他在虚空中説:“閻王拿我金璧峰,猶如鐵練鎖虚空;鐵練鎖得虚空住,方可拿我金璧峰。”很好的。你們想想:你們的本事再大,天上還躲得住?地下更不要説;虚空裏躲不住,虚空外也躲不住;唯有一個“念佛是誰”能躲得住。躲在“念佛是誰”裏,任他閻王老子本事再大,亦不能奈你何!釋迦老子也不能奈你何!“念佛是誰”還要緊嗎?參!
十一月十八日開示(伍七第五日)
初發心用功,怕妄想;工夫用久,怕昏沉。這是甚麼道理呢?因為,你們全在昏沉、妄想裏做活計,説怕妄想,怕昏沉,“怕”的那個東西,亦是昏沉、妄想做的。怕妄想,不打妄想,還是妄想;怕昏沉,不落昏沉,還是昏沉;你們還曉得嗎?大概不容易!雖可以説你們現在打七用功超過平常幾倍,一個七要超過平常三年。但是,用功的一句話,有種種差別:其中有身精進、心不精進,有心精進、身不精進,有身心俱精進,有身心俱不精進,四種差別。如何是身精進?就是行香、坐香不同:行香,飛跑;坐香,外面好得很,心裏還是昏沉、妄想。心精進者,就是一天到晚,心上“念佛是誰”歷歷明明的;外面行香、坐香平平常常的。身心俱不精進這種人,無須多説,六道輪迴是他的好窠臼。如何是身心俱精進?這一種人,行香、坐香是有精神;心地上清清楚楚的,“念佛是誰”時刻不離。若有這一種工夫一天到晚的用,一個七打下來,决定超過平常三年。這麼講,不是超過心精進、身不精進的一種人?假使光對那身精進的人講,超過三十年還要多!再説身心俱不精進的人,更安不上。我雖是這麼講,要你們從自己心行上討論一下子,在七期裏是那一種的精進?不是小事!凡是有心用功的人,應當檢討的。你們平常一年三百六十日,天天俱是身心精進,莫説一個七、十個七,再多也不能超過你這一種人。大家要研究一下子,不是馬馬虎虎的,莫説平常,就是打七也然。但是,現在你們七打了五個下來,身上的精進早已放下來了:跑起香來,兩隻腳拖不動;坐起香來,腰一彎,爬下來了;一天到晚捱命似的。問到你們“念佛是誰”?倒要説:“參够了!”弄不出一個名堂來。起疑情,更够了,一起,起不起;再起,還是起不起。够了!與身,與心,與“念佛是誰”,與疑情,總是一個够了;工夫是完全拋得光光的。這也是好事。但是,要光纔好,恐怕你這頭拋得光光的,那頭到又堆滿了,那裏得光?終歸有一頭:不在這頭,就在那頭。究竟那頭堆滿的是甚麼東西?無非是打妄想,翻業障。七打了五個下來,你把“念佛是誰”拋掉,不顧用功,這個妄想,那個業障,多得很!十年、二十年以前,乃至做小孩的事,通通翻出來,緊翻、緊翻,翻得很有味道。你們站在這裏,聽我講的對不對?你們這樣的人,“精進”兩個字還安得上嗎?工夫用不上,有甚麼事?當然要打妄想,翻翻業障。你這一種妄想同業障翻起來,連你本形都忘了!上海、南京,紅的、緑的,男的、女的,盡氣魄、盡力量的去打。未打七以前,似乎還有一點把握,在用功時,心裏打起妄想來還有點底止。不談開悟,對於工夫絲毫的名堂也没有,這個妄想還有底止嗎?你們若是這個樣子下去,我替你們真可惜!可惜到淌眼淚!未用功以前,業障高如須彌山,厚如大地;現在把“念佛是誰”今天也擦,明天也磨,似乎少了一點;今天忽然大翻一下子,這一來,恐怕比從前還高、還厚一點。譬如:一個人老欠人的債,今天也想法還,明天也想法還,還了多時,還得差不多了;忽然把錢一賭,輸了一筆,倒比前債還多。對不對?妄想、業障還能由它翻嗎?工夫用不上,還能隨它去嗎?但是,你們現在忘形、忘體的翻起業障來,也可以有回頭的一天;你久久的打,久久的翻,有一天翻够了,回過頭來,纔知道我是一個出家人,是住高旻禪堂的!一個人到了那個時候,太遲了。所以要你們早點覺悟纔好,債拉多了要多還,業障翻多了要多加生死。還有甚麼別的話講?再則,妄想、業障在這個時候不許翻,將來到了一個時候,還要你們翻,非翻不可;現在翻,有罪過,那個時候翻,没得罪過,還有功。這是甚麼道理?是你們工夫上的程序,行到那裏,是那裏的事。甚麼時候可以打妄想?要你做到工夫落堂自在;那個時候,你不翻還要你翻,非翻不可。假若不翻,又不對,非宗門事了。甚麼道理?你工夫用到那個時候,若不翻,反被工夫障住了。你還曉得嗎?那落堂的工夫,是甚麼境界?就是把“念佛是誰”做到與現在打妄想一樣;現在一天到晚在妄想裏,不打妄想也在妄想裏。到了工夫落堂的時候,抬起頭來“念佛是誰”,動起腳來“念佛是誰”,舉心是“念佛是誰”,動念亦是“念佛是誰”……總之,要起一個別的念頭,是做不到,了不可得。工夫到了這個地方,忘想想打,打不起;業障要翻,翻不起;任是天翻地覆,要想離“念佛是誰”不可以。若就住在這個地方又不對,必須還要向前走。“怎麼向前呢?天翻地覆,要想動個念頭了不可得,再向前走?”若是没處走,不要你走;此時纔許你們打妄想,翻業障,緊打,緊翻,越多越好。何以呢?這個時候,打一個妄想,少一個妄想;翻一個業障,少一個業障。妄想、業障若要不打、不翻,又被工夫蓋住了,終歸不行;打了、翻了,纔算無事。譬如:一窩大盗,有五六個人,一年到頭都是偷人家的東西;今天偷了一個茶壺,放在家裏;明天偷一個酒壺,放在家裏;你偷雨傘,他偷帽子,一齊的在窩裏藏得滿滿的。偷久了,有一天被人家降住了。降了以後,很好的,很太平的,好雖好,還有臟在,還有窩子在;若不把臟翻出去,窩子打破,不久,強盗又要住進來。你把他的臟也翻了,窩子放火燒光,強盗再來,住甚麼地方?豈不是永遠太平?工夫亦如剿匪一樣。強盗是甚麼?就是你們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;偷的東西,就是妄想、業障;剿匪的人,就是“念佛是誰”。今天也參,明天也參,首先,是外境界、內妄想力量大得很,眼一動,“念佛是誰”丟了;耳一動,丟了;乃至身、意等亦復動即丟了。久久的用功,眼再動,“念佛是誰”亦在;耳再動,“念佛是誰”亦在;乃至身、意等再動,“念佛是誰”還在;又如強盗降了,工夫落堂自在。雖然工夫落堂,強盗已降,臟還在,窩子還在;所以要你再打妄想,翻業障,翻一個少一個,就如把臟物一件、一件向外拿,把它拿了,就可以把窩子打破;破了這個時候,是真太平。但是,我要問你們:太平以後還有事嗎?恐怕倒又不曉得了!那麼,落堂的工夫,你還没有用到,窩破、臟盡的事,更没有用到,再向後的事説也無用。等你們工夫用到了這裏,我再與你們講。現在回過頭來,再與你們説:現在的工夫,就是工夫用不上,妄想非打不可,業障翻了還要翻;“念佛是誰”降也降不住,一降、再降,更降不住,没得辦法。因為,你要降它,這一個要降它的心一起,更是妄上加妄,業上加業,那裏會降得住?你就是一個不睬它,不理它,不降它,不壓它;終歸我的“念佛是誰”可以參,不斷的追究,自然會上路。這是正要緊,要緊!發起心來──參!
十一月十九日開示(伍七第六日)
工夫的程序大概有三種:第一極生,第二極熟,第三非凡、非聖。這三個題目,把你們用功的程序,一概包盡;任你工夫用到甚麼樣,不出此三種。極生的工夫,大家都可見到:“念佛是誰”擺不進,你要參,“念佛是誰”被妄想擋得牢牢的;再提一句,妄想奮勇起來,被它一勇,一枝香,二枝香,没有斷頭;照常一天、半天不得斷頭。忽然想起來,再提一句二句,昏沉又來了,睡了半天纔知道;再提,業障、音聲、色相,身上的痛癢……乃至一切處,都是打失“念佛是誰”的一種對境。甚麼道理?因為它們熟透了,工夫生透了;並没有甚麼奧妙,衹要久提、久參。現在,七打了五個下來,不能説是極生,一定有點進步;雖還没到極熟的地方,總是這麼用,任是再生,提起來就不放鬆;久久的,一天有半天工夫,這半天雖還是聲色、妄想的打岔;但那半天把得住。在這個工夫上,再考究一個得力不得力,念佛的是甚麼人?不曉得;再問:到底是誰呢?這一追問,不明白不行,總要問過明白纔放手。就在這個地方緊問,不交代我明白,總不放手;這麼老問,回過頭來一看,工夫有點力;再檢點一下子,我這身還在嗎?似乎身上的事,身外的事都没交涉。子細的一考究,身體似乎没有了,我這一個身體既然没有,音聲、色相、痛癢,安到哪裏?工夫慢慢的用,一時半刻身雖没有,似乎還有一個二個妄想、業障還突突的要出來的樣子。這是甚麼?心還没有去掉;還要“念佛是誰”不放鬆地參。久久的,妄想打不起來了,業障的影子都没有了;衹有一個“念佛是誰”不明白處,到了這裏,心亦不可得了。身忘了,心亦忘了,身心俱忘,任你再好的色,再好的音,没有身,它在甚麼地方落腳?不怕情愛再深再厚,没有心,它在甚麼處安身?身、心俱不可得,可算工夫現前,亦是工夫極熟。極生是凡夫;極熟並非聖人,亦不是非凡、非聖的工夫。工夫現前,是個甚麼境界?要你們自己走到這個地方,自己會見到;我與你講到,你不行到,也是白講!因為你們太可憐!對於用功的前途,没有一點把握,不能不替你們略講一下子。工夫現前:就是“念佛是誰”現前;任你行、住、坐、卧,打妄想,翻業障,俱是“念佛是誰”。就如你們極生的時候打妄想一樣:行住坐卧,在妄想裏;舉心、動念,在妄想裏;穿衣、吃飯,在妄想裏;提“念佛是誰”亦是妄想;怕妄想、除妄想更是妄想。今天,工夫現前,一切處皆是工夫,任是打妄想,翻業障,俱是工夫;這樣,就是工夫現前,亦是極熟。不能就算了事,還要生不可得,熟也不可得;生、熟俱不可得,纔算到了非凡、非聖處。那麼,在工夫現前的時候,就是個“念佛是誰”嗎?你們不要會錯了,到了這個地方,衹有“念佛是誰”不明白處,還衹許一個不明白,不許有思量處;亦不是胡胡塗塗的不明白,亦不是馬馬虎虎的不明白:這纔是工夫現前。甚麼道理呢?趙州老人講:“老僧三十年不雜用心,穿衣、吃飯是雜用心處。天下人在明白處,衹有老僧一人在不明白處。”這就是一個鐵證。那麼,到了這裏,可算到家嗎?没有,可説生死的輪子停住了;就等於停住的車盤一樣,不轉就是,還不能算了事。再進一步,到了那個時候,我們談談家常話,説説家裏的事;現在説的、講的不是家裏事,是路上的事,是指路碑。你們還不曉得罷!宗門下的事,轉凡夫成聖人,不是究竟事,不是宗門下的特長處;何以呢?聖人地位是途中事,到家的事仍隔一程。你們還能領會一點嗎?若能行到這裏,方許是宗門下的事,是宗門下的特長。這一句話衹許宗門下講,其他一切法門不許講;這是極熟以後,一層一層的事;雖然説到你們聽,大概不容易領會,就是由生轉熟,善根少的人還有點滯礙。我再説個譬喻你們聽聽:我們一堂的人住久了,行香、坐香毫無奇特;忽然來了一個紅頭洋人,鼻子很高,眼眶很深,塊頭很大,一切與衆不同;你們大家的眼睛向他望,他的眼睛也向你們望,你看他是奇特,他看你也是奇特。跟進跟出,你又不能向他講話,他亦不能向你講話;他一個人坐也不敢坐,吃飯更不敢吃。久了,你望他一笑,他也向你一笑;再久了,説一兩句話;再久,熟了,不奇特了,彼此都熟了。再久,打同參;再久,不對了!他倒欺負我們了,每一舉動,要聽他指揮;再久,反過頭來,向他磕頭了。你們大家想想:世間上的事,是不是這個樣子?今人的常情,亦是這個樣子,工夫下手亦是如此。一堂的人猶如妄想、業障,一向的習氣熟得很;紅頭洋人即“念佛是誰”,是生的。下手用功的時間,是不是提起“念佛是誰”來,妄想就涌起來?就如你們大家看見洋人,一齊將眼望到他身上一樣。久久熟了,當然也可以參參。再久,參也好,不參也好;妄想打也好,不打也好;打同參了。再久,妄想站不住了;“念佛是誰”為主了,為王了。是不是世界上有這個道理?用功亦是如此。你們真可憐!太苦惱!一個“念佛是誰”,到今天還有人不相信,是不是苦惱?大家都是明白人,我勸你在“念佛是誰”上多吃一番苦,多受一點委屈,與辦道纔有點相應。參!
十一月二十日開示(伍七第七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