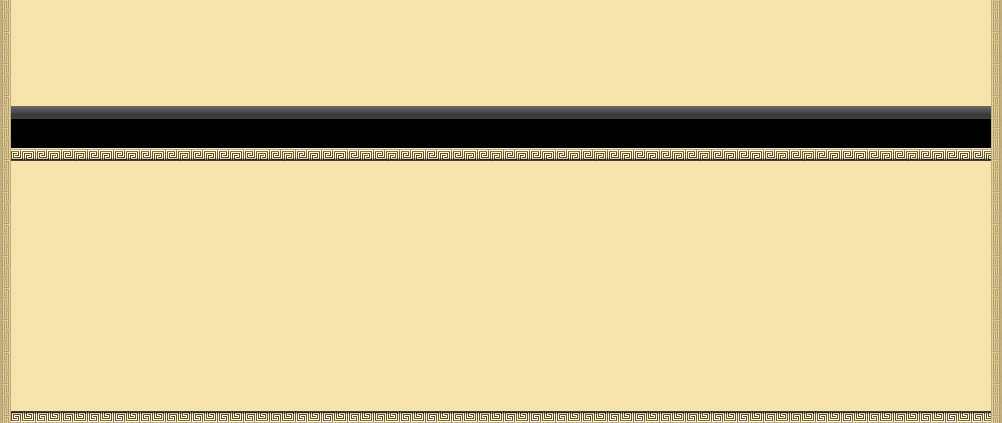自願以悟爲期,不悟不出禪堂;立行不倒單、不告病假、香假、縫補假、經行假、殿假;寧死在禪堂,不死在外寮;單參“念佛是誰”一法,毫無其他妄念。初住禪堂,規矩不會,從早四板至點心時,挨三百餘香板,衹是半天,至開大靜候,共(身+卑)![]() 四百多下香板,毫無煩念。勞動執事,攪擾大衆,深加慚愧。由是留心學習,大規矩、小法則,堂內、堂外,默背透熟;規矩熟後,安心辦道,任人見不到我眼珠,聽不到我音聲,未見我掉一回頭。
四百多下香板,毫無煩念。勞動執事,攪擾大衆,深加慚愧。由是留心學習,大規矩、小法則,堂內、堂外,默背透熟;規矩熟後,安心辦道,任人見不到我眼珠,聽不到我音聲,未見我掉一回頭。
一日洗澡歸,至大殿門,忽掉面向內一望,即被丈室小价哩(口+赖)![]() 一頓,他開口云:“放逸。”我著一望,是一小价,慚愧以極。至大靜後,打耳巴子七八下,痛責自己。
一頓,他開口云:“放逸。”我著一望,是一小价,慚愧以極。至大靜後,打耳巴子七八下,痛責自己。
又一日,人問我:“大殿供的甚麽佛相?”不能答;再追云:“可有鬍子麽?”亦不能答,因我向未舉頭上望。
一日,齋堂受供,工夫得力,碗舉起不動者,約五分鍾;偶被僧值一耳巴子,連碗帶筷子一齊下地,衣袍悉沾湯水,碗破數塊。工夫把住,不許打失!由是迄今,我住地方,齋堂不准執事打耳巴子,即此來因。縱有要講,等候初八、二十三、十四、三十日,正當講之,從朝至暮,日無虚度,夜無暇晷。
每放香時,東西兩單,來我位前,請示問話,周圍一轉,廣單上下,亦有人圍聽。至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曰,晚六支香,開靜(木+魚)![]() 子一下,猛然豁落,如千觔擔子頓下,打失娘生鼻孔,大哭不止。悲歎無既,瞞到今天,沉没輪回,枉受苦楚。哀哉,痛哉!無限悲思,歎何能及!次日,到班首處請開示時,前所礙滯之言,迄無半句。班首云:“汝是悟了語句。”即問:“念佛是誰?”應答如流,又問“生從何來?死從何去?”等等,隨問隨答,了無阻滯。不多日,和尚、班首臨堂贊頌,我即搭衣持具,向各寮求懺悔,止其莫贊。
子一下,猛然豁落,如千觔擔子頓下,打失娘生鼻孔,大哭不止。悲歎無既,瞞到今天,沉没輪回,枉受苦楚。哀哉,痛哉!無限悲思,歎何能及!次日,到班首處請開示時,前所礙滯之言,迄無半句。班首云:“汝是悟了語句。”即問:“念佛是誰?”應答如流,又問“生從何來?死從何去?”等等,隨問隨答,了無阻滯。不多日,和尚、班首臨堂贊頌,我即搭衣持具,向各寮求懺悔,止其莫贊。
一日,慈本老人舉手巾作洗臉勢,問我:“是甚麽?”我云:“多了一條手巾,請將手巾放下。”彼不答而退。自此益加仔細,不敢妄自承當,苦心用工,必多見人,以免自大。由是日行倍加密切,一聽維那報坡,勢同搶寶;凡有公務、行單各事,置身不顧,操作敏捷,辦事精詳,爲衆人冠。
至宣統二年春,請堂主執,未允。凡外寮行單,悉公務盡,上至和尚,下至打掃,所有規矩倒背如流。我在規矩上用心,其義有二:一、當知叢林規矩爲行人悟心大法,見性宏模,現爲行法基礎,未來爲進道階漸,一也;人能留心規矩,巨細清明,毫無訛謬,自則為立身大本,他則為拔楔抽釘,一旦受執為人,拈來便用,二也。
我一日住西單尾,有人來我處問話,鄰單嫉妒,即用醒板打我數十下。維那得知,進堂問我:“誰個打你?”
我即白曰:“是鄰單一位師傅學打香板,在我肩上學之。”
悦衆抱氣不平,即云:“是某人打他。”
我即曰:“不是。”
維那未深追,否則,這位鄰單師傅命送一半。此我學德之密處,故我自用心法稍得益後,專門習學內外規則,日無倦態。
至夏,常住復請班首,自思:受戒迄今,不過四年,何能擔此重任?自願大寮當飯頭。時值隱老戒期;往年戒期,飯頭三個,大寮馊飯缸一口,馊菜、馊粥缸各一口,至我當飯頭,衹我一人,馊物各缸,不存大寮。一戒期滿,未剩粒米;粥飯菜蔬,亦未抛散,想法辦好,與大衆吃。據庫執云:“今年戒期,要省九擔米。”戒期單銀及供衆等款,掃數結新戒緣,多馀之款,辦一凉櫥,現存未朽。
一日飯將炒好,妙首座和尚把住鍋鏟柄,答應當班首可放手,不允不放手。我乃急死,再遲一刻,飯不能吃,衹好答應,委屈求全。滿期後,至期頭,本擬進堂,實因學年太淺,怕當執事,私向水頭師借四角小洋,逃來高旻。此宣統二年四月三十曰事也。
外面聞到一金山、二高旻,諒高旻不遜金山。一到山門,即生退心,何以?大門是爛洋鐵包的,又加缺破;進門兩邊,石塊、瓦渣、青草擋路,用世人眼見,實無安住進取。再思古人之道及用工之人,此處足稱最上上之道場也。何以?儒人求道,食無求飽,居無求安;禪人用工,自己向不許有,其他何以究竟?我何人也?其不愧乎?由是奮發精進,安住禪堂。夏天居衆不多者,因各處經期、戒期、會期、佛期、看師、省親等等,故衹有三四人過夏者,亦有十餘人過夏者,或三二十人過夏不等。一日,請月朗定祖開示,問答相投,即厲聲曰:“萬要苦住高旻,不可亂動,汝若溜到外國,我定要把你找回,任你上天,我用烟把你熏下,好好回去,善自護持。”誰知這一次開示請過,上了高旻圈套;不多時,請我當班首,百計推卸不許,義不容辭,勉允之。
受執事後,禪堂凡出坡各事,皆我一人擔負,不勞大衆以及客、庫寮事;棘手者,我一肩夯。至是,放手大做,儘量培福,當仁不讓。
一日,外面有冒名僧數十,威威赫赫來寺,各執事被迫潛藏,和尚急召我出;至客堂,將他來文閱悉,即婉言勸走,彼拒不肯去,口中漫駡,如何若何。我即大聲喊數小工出,抱綑繩子來,云:“一齊捆好,抬到三岔河裏,送身水葬。”彼等駭得飛跑,携來各件,不及帶去,直奔出外,同伏坐下,嗟歎曰:“這個好大冒勢鬼!不是跑得快,險險被他捉住。”自是奄奄回去。
我這一面把躲藏的各執一一招呼出來,仍做各事;那一面,著人出外,探詢事態何如?據回報云:“他等一到高旻,看到有道德氣象,實不敢妄動。‘加之有個妙堂主,比閻王老子還狠,我們不是跑得快,險險吃苦,勸你們不必勞神。’”我言:到某處了生死,我們欲想天下叢林怎樣,反遭大過。何以一進寺門,似像有神擋路,或似有鬼催走,思之龍天大道場,定有神護等語。此一九一二年四月間事也。
我在禪堂,受執班首,上殿、過堂、出坡、行香、坐香,與堂師同一起到,未離堂師一步,堂中大規矩、小法則比人熟,色力比人健,精神比人強,講話比人清,調衆比人順。由此各事過人,難免有礙人事,任是前後執事嫉妒,我不理;表我的堂,更不理;提我名字收拾我,亦不理。
一日,有一位執事,當衆吼我,我與他磕響頭;至晚,請他到西寮明間設位,請他上坐,特裝三支香,向他磕三個頭,請他向後再表我的堂,求他不要提我名字。一日,我後一位執事又講我,我急到寮房,弄一團棉花,把耳朵塞好。前人吼我者,即裝香磕響頭;後人講我者,弄棉花塞耳朵。我有誓在先:寧死溝壑,不在禪堂與人交口争鬭,若稍違逆,以誓證盟。每有人言,妙堂皮(皮應作脾)氣如洋火,到未聽見與人打個(占-口+又)![]() 扎。任人不知,我有成竹在胸——凡報坡夯柴火,別人二人抬一綑,我一人夯兩綑;出坡夯稻,別人二人抬一籮,我一人挑兩籮;禪堂大衆衣服、被條,盡歸我洗,成就人用工;油盆桶、洗竹墊,不准人到,概我一人。
扎。任人不知,我有成竹在胸——凡報坡夯柴火,別人二人抬一綑,我一人夯兩綑;出坡夯稻,別人二人抬一籮,我一人挑兩籮;禪堂大衆衣服、被條,盡歸我洗,成就人用工;油盆桶、洗竹墊,不准人到,概我一人。
我寮床上被條,龍含珠放當中,亳無其他零細。棹上一塊香板,現在規約一本,其餘茶壺、杯子、油燈、油壺、佛像經書,紙筆墨硯、香爐燭台、大小各物,一概不存;任是堂內外人,寄存錢鈔、衣物,拒絶。內清外净,了無罣礙,自則身心瀟灑,人見似有古風,此身外莊嚴,斷不能少。
每有金山,暗著人來,勸到江天寺。一九一四年正月期頭,金山請堂主執,辦事時長,諸凡生厭,擬棄叢林,遁居深山。至三月二十四日,約同傳恒師,徑赴終南,隱居湘子洞。居洞情景,容後再叙。
至一九一五年夏,金山慈、融二老,特派普堂主持親筆函,急催回鎮;高旻月老用揚州諸山名義來函,電匯路費四十元,亦催我回寺。金山、高旻函電紛馳,殊無回意,我在洞願死於山崖,埋於溝壑,不願南返。至是,各茅蓬得訊,勸歸甚力。
一日,持袋取米,將出湘子洞不遠,由山頂忽滚一石,轟轟烈烈直下,正落身後,離腳五寸許,當時駭得精神衰喪!取米歸,將至洞外,復滚一大石,置於我前,離身尺許,一陣冷風,魂駭離體。至洞奄奄危坐,五內不安,拴龍樁。有
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二日回寺,依法巡寮。禮月祖時,月老有病,一手抓住,死不放手,即命現任住持明老擇期傳法。和尚云:“請老和尚看日期。”月祖云:“就本月十五日。”和尚依而行之,隨請諸山,如期雲集。
傳法後,月祖止我他去,侍奉巾瓶。至十六日,復令和尚悉在床侍奉。十六晚,親令和尚打二磬,呼我敲小(木+魚)![]() 子,同聲念“本師釋迦牟尼佛”;至晚八點鍾,招手止念,單呼和尚云:“你向來脾氣不純,對妙後堂,須特加優容,不可苛刻;你可著住外寮,一同護持常住,要緊!你們念吧!”念約兩點鐘時,招手歇佛,令我請堂內班首上來,一一向其合掌告假,衆人舉目罔措。告假畢,請衆執回寮,復齊聲念佛,念約點鐘,招手止念,抓我手云:“你雖接過法,我還不放心,要你發一誓願,我纔放手;若不發願,我死不放你手。”月祖言畢,不令念佛,候我發願;我正難時,月祖即云:“要你講生是高旻的人,死是高旻的鬼。”躊躇多時,勉強答應,月祖還不放手,又令念佛,要你講,生是高旻的人,死是高旻的鬼,躇躊多時,勉強答應;還不放手,又令念佛。至十七日早課下殿,手還未放,我覺駭怕,漸漸冰冷,我疑恐不開,請人雙手力推,始放手;如冰凍一塊,貼我手上,約五分鍾落氣,我即與洗澡、裝缸。此一九一五年事也。
子,同聲念“本師釋迦牟尼佛”;至晚八點鍾,招手止念,單呼和尚云:“你向來脾氣不純,對妙後堂,須特加優容,不可苛刻;你可著住外寮,一同護持常住,要緊!你們念吧!”念約兩點鐘時,招手歇佛,令我請堂內班首上來,一一向其合掌告假,衆人舉目罔措。告假畢,請衆執回寮,復齊聲念佛,念約點鐘,招手止念,抓我手云:“你雖接過法,我還不放心,要你發一誓願,我纔放手;若不發願,我死不放你手。”月祖言畢,不令念佛,候我發願;我正難時,月祖即云:“要你講生是高旻的人,死是高旻的鬼。”躊躇多時,勉強答應,月祖還不放手,又令念佛,要你講,生是高旻的人,死是高旻的鬼,躇躊多時,勉強答應;還不放手,又令念佛。至十七日早課下殿,手還未放,我覺駭怕,漸漸冰冷,我疑恐不開,請人雙手力推,始放手;如冰凍一塊,貼我手上,約五分鍾落氣,我即與洗澡、裝缸。此一九一五年事也。
至我接住,每有困難事,焦愁於心,夜即現身,向我指示者多次。夢中見到,如在生,黄袍白鬚,持杖居我對面,説畢不現;誠不忘高旻,不負我意也。
雖接法未久,各事完全擔負,尤慮工夫未透,預再參方。至一九一六年,到常州天寧進堂半日,即請班首未允,高旻來人催回,幫收秋租及理訟事。至一九一七年,復參天童,受後堂執。一九一八年夏,受維那執,秋至福建雪峰受後堂執,掩生死關,任死不出關。
至一九一九年夏,混身水腫,行坐不便,高旻來函催回,函云“如萬一不回,即派人來,路費歸我,因果歸你”等云。由是束裝來揚,六月初四接位。二十四日,先造柴火房,因大寮不寬,柴火儘堆竈門,稍一大意,火延上堆,每年到大寮打火者數次。思之,其他一切修造,無關重要,堆柴草處,最爲吃緊,是故興工,竈外起房一間。至動工時,未擇日期,夜間夢中,見穿藍衫差使立我前云:“太歲官請你去講話。”我拒不肯去,他就動拖,我急跪在破土之亂泥石塊中磕響頭,他云:“不必,我替你講講看。”他走,我醒。一覺思之:此處動土犯太歲,再翻年曆,查出毫不訛謬。我一向不信算命卜卦、陰陽地理、打銀針、貼膏藥、降神問籤,不但不信,時而輕視。由此看來,不能不信,否則被他拖去,下文不知所以。以後無論大小工程,欲動工者,或看曆書方向,能動則動,自此一切相信。
又東放生河,上年有人醞釀,擬爲公有,九月初,事方暴露,彼方先派人來寺查詢,彼限七天答覆,否則勘估報領。我在急迫中,翻找各處,忽找一包,外批“內係雜碎紙”,拆開一看,內有門板大的一張告示,係南京總督部堂高,施爲高旻寺作放生河之用,又找出此河免錢糧執照一張,心纔放下。我即時快函到北京請我至友,專函到縣,急爲出示保護,免夜長夢多。
七天將到,調查人來寺,即將告示與執照交看,雖收藏好,彼等當下無言對復,即云:“汝有充分證據,回報後聽復。”至一月餘,北京來函,同地方紳董,請給告示,文件送寺,即勒石永禁私人覬觎等情,石碑上墻永爲寺産,誠係鐵證。此一九一九事也。
清明掃塔,爲僧家順世之道。我在一九一九年時,探詢高旻中興天慧徹祖之塔安於何處?據我法師明公談及:天祖塔院在常州扁擔河,自咸豐迄今,無人到過。光緒三十四年,楚祖老人,往查一次,找三天纔尋到,認實無訛;彼處當家否認,高旻祖塔反被他羞辱,掃興而歸。至次年,同月朗定祖再去,即將房屋用具,各件清單帶回。至臨行時,月祖云“不久擇期修復塔院”等語,彼當家云:“汝放木料來,我當阻止興工,令你原璧歸趙。”二老又悲痛而歸。由是輾轉住持,多未聞問。
至我法師明公和尚,我問云:“老和尚可去過麼?”他曰:“月、楚二位老人去過,尚是冒險而歸,我何敢去。”云云,我聞之心生痛切。高旻之興,必飲水思源,既是祖塔,豈肯被人占去?祖心何忍?我於六月初,帶一小价,挑供菜籃,直到奔牛。一路問人,皆不知有揚州高旻之塔,找到第三天,順扁擔河東邊,走到望到路邊照壁墙外,書“磬山寺”三字,歇下進內,見一新戒禮接,我云:“當家在家嗎?”
他云:“不在家。”
我令他趕快弄飯,“你的當家,把我塔院污糟不堪,今天要同他講話。”新戒是前住持之徒,正與現當家不睦,聽我説要辦他,他將塔院情况和盤托出,急弄飯菜,先在塔前上供,我即私派小价,四處翻挖;不多時,挖出高旻石碑六塊,洗清,知是天組語錄後之傳法語句,我依舊用土蓋好。
供上好,碑蓋畢,當家回寺,著我一望,我即厲聲正色曰“你當家做甚麽事?把我塔院弄到這種樣子”等云。
當家又私聽到新戒講:“高旻和尚要辦你。”當家急轉風頭云:“對不起!少迎接。”他云:“自從接任以來,未到奔牛一回,將將頭一次,和尚就來了。”他即順住我講話。
我囑云:“今天要走,塔院、田地、山場各件,若有人侵佔或偷竊,你急到高旻報告,少一分田,我就不答應。”
彼云:“請放心。”又將挖出之碑,令他保存好了,他一見碑,魂不附體——自此是收塔院之鐵證也。
至九月初,該當家與新戒涉訟告官,新戒告他:家養女人,吃葷喝酒,帶吃烏烟,外加嫖賭;當家告新戒:偷塔院牛一條、小麥四擔、稻子九擔。新戒知事要敗,急將牛、麥、稻交一半與董事,請出理楚。董事急將原由來函高旻。
當家穿老黄色袍子來高旻找我,我當時不能會,會則鬆脛。睹此事態,會辦與否,就在這些關門過節處著眼,隨派人代向他云:“你趕快回去,急將所失各物,一律追回,如少一件,與你有大關礙。”我候他回家,一封信與董事,不能過問寺事;常住依照共住恒規,當家養女人犯淫戒,急應驅逐;新戒偷牛、麥,犯盗戒,應當遷單。不日派人來塔院,遷兩人單,即理偷竊事。
這封信去後,董事一見,立即躲藏,該二人一齊逃跑。派人去看,無一人在塔院,平安收回,未用一文,未勞一人。董事有牛麥關係,怕我深追,故躲;該二人怕我辦他遷單,故躲。不但收回天祖塔院,加之收租田四十餘畝,如此順手,諒有天祖幫忙。此一九二零年事也。
寺西行宮,原係順治時,鹽商諸總情借寺西餘地,修建行宮;至咸豐間,行宮寺塔均遭毀壞,舊有錢糧,照完無欠。近有私人,藉行宮之名,誤認公産,凶(凶同汹)涌來寺,預爲勘估,牽繩帶索,有急急不能終日之勢。復召我到場聽諭,膽稍小之人,直被駭得要哭。我於次日早,私往上海,找信佛同仁,急電縣府,制止報領等情。縣飭江都官産駐辦員禁止私人擅在高旻寺丈量估看,有擾亂僧人道念等情,由此告一段落。此一九二一年事也。
此時叢林,不酬應經懺佛事者不多;有齋主人情關係應酬者,有靠經懺生活者。高旻雖專門禪宗,每年水陸三兩堂,焰口數十臺,大小經懺亦有,唯有萬年水陸一堂,勿論如何,非做不可。
一日因事往申,
每至清明掃塔,對於天祖院基,荒蕪破亂、污穢不堪,兼是草房小而且漏,故特往常州,呈文縣府,請給示諭,保護開工,隨即派人至鎮,採辦木料,定購磚瓦。二月二十二日,破土興工,依照舊有房腳砌墙,前後兩進,東西兩廂,塔外六角亭一座,至十一月竣工;內修天祖原像,前殿供王靈官。是年置田與贖田,及原有田共約六十馀畝。自此以後,天祖香火,綿綿無間,蔭庇高旻,將無窮盡。此一九二三年事也。
斷而復續之行宮,欲圖取利之人,從事恫嚇、藉端欺許。有人調處約用少款,儘可了事者;又有人替我包辦,不費多錢,准在官廳注銷者。欲取漁利之人,不在少數。視此無妥善辦法,終難徹底永久解决;我即往申,找原起事人,作一勞永逸辦法;請人去函省方,派官産處饬江都駐辦員,嚴查確實,實是寺産,毫無疑義等云。由是省長、官産處長、江都縣長,根據寺存,雍正九年上諭、將行宮還高旻寺之憲票,合行出示,勒石永遼保護。自此根本打銷,大碑上墙,昭諸遐邇。從興事至了事,除往返川資外,其餘未用分文,此亦大幸事也。
高旻有普佛,皆隨早晚殿,某他一切佛事,概不應酬。一日,揚州張護法擬早二板打延生普佛一堂,他云:“出普佛儀二百四十元。”要求我放早板香一枝。我云:“居士當知:寧動千江水,莫動道人心;若放香做佛事,居士不但無功,反爲有過。”
居士來氣云:“二百四十元不肯,出二千四百元,諒必准念嗎?”
我亦氣云:“任是二萬四千元,亦不能打普佛。”由是不顧感情,掃興而止,帶歡笑曰:“和尚是鐵打的規矩,如是行去,我很佩服。”云云。自此,任何人欲將錢買放一枝香,萬難做到。
是年即將萬年水陸,改净七一堂。水陸約共四十馀人做佛事,牌位每座一百元;净七約二百余人打七,大殿、外寮早晚殿二次回向,牌位每座二百元。恐前有牌位之人,不願打七者,僅可還款;願續供者,情免加錢。由是經懺佛事之根蒂,從此永絶。此一九二四年事也。
農人收獲將竟,所有車桶、車軸各件,悉數送寺,由天王殿及兩廊擺滿,無插足處;寶應、慈云庵,倉房亦然。實有污穢伽藍,剌人眼目,即設法包歸佃户:江都田車,每車篷包費五元;橋梁涵洞,百包在內,腳車二元五角;寶應每車,歸佃修油收藏,約定一九二四年滿,再换新車。寺與佃有騎縫印根條,以根條為换車證據。自此山門清净,廊路寬宏,大壯瞻觀,佛天生喜,實减少無限煩擾也。又常住既無佛事,寺內寺外,當然徹底清凈,不受金錢勢力之所強迫者。故三岔河由關,每年七月上旬,請常住放利孤焰口一堂,復借用寺之長桌、短凳各件,約一百餘年之歷史習慣,未少一次。我事前預爲通報該關賬房,今年無放焰口之人,亦無焰口臺上用物,因霉爛破碎辭之,請另找他人代放。幸而至時,不復來寺邀約,由是經懺根子拔盡。此一九二五年事也。
由關在邇,辦事人員藉此名目,任何人來寺,常住必恭而敬之,熱心招待,間有弄花果、要竹木:“請問你是那裏?”
彼答:“我是關上。”
寺執一聞“關上”二字,趕快與其辦好,率以為常。我思之,該處非法律機關,亦非治安地位,殊無保障性質。每至六月,荷花開時,預先持帖,上下請到。客來招待後,執事陪同玩賞荷花畢,回廳吃齋,名“荷花齋”,共約十席左右。最感困難者,擇定日期,筵席辦好,衹等人吃。天稍凉時,十席不够;天稍熱時,三席不足。所剩菜蔬,過時則馊。再感麻煩者,後三五日,天復稍凉,不請而至。一陣半陣,趕至客廳,招待稍疏,出言不遜,以此視僧人為用人者,不符大雅。由是事前報知,今年荷花齋,敝寺無能為力,一候稍長,再爲補報。至是如期未辦,亦未稍争。此齋乃月祖請藏經擬化關上稅款,帶收少分,補請藏經各用,前立經褶,三節持摺,到關取款,或三千文或五千文,徵末之至。荷花齋有三十八年之久,今一免永免。此一九二六年事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