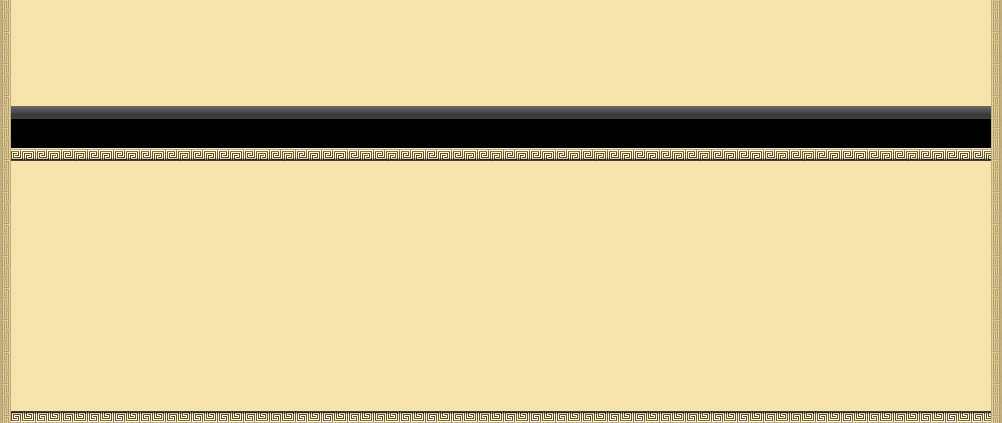自行錄
余僧俗籍湖北省黄岡縣,俗家劉姓,父諱嘉缜,母氏方;俗名永理,字福庭,祖上耕讀爲業。母懷妊時,不能食葷,吃則腹痛;至臨産夜,父見金鯉進房,母見黄袍白鬚老比丘入內,滿屋通黄,不半時,余誕生矣。父命名叫鯉,母取名叫小和尚;父知鯉字乃孔聖人子名,早死,故遂改理。
出胎後,母乳不能食,僱素乳母;不二年,愛吃鹽炒乾飯。
至三四歲時,喜捏泥土佛像,供於田岸土洞中,日往禮拜者數次;其他,非性之愜與。
至五歲時,父授初學書本,不一年,悉能背誦如流。至七歲時在鄰廟攻書,有外道求我,告以《心經》,至無智亦無得,無人無我相,豁然省悟,堅萌出家之念。至九歲時,外道請我先生,告《高王經》,經中阿閦佛之“閦”字,先生授一“閃”字,復問我,我云:“不是‘閃’字,是‘閦’字。”比
從七歲起,每晨待旭日初升時,誦《心經》七遍,日暮時,誦《心經》七遍,習以爲常。放學途中,見老者,即悲而歎曰:“你死後安身何處哦!”老人顧盻,又一笑置之;見年輕婦女,即恨曰:“弄這多花粉塗在臉上,幻作妖嬈,而身上臭烘烘的,粉再多也蓋不住。”一遇女人對走,我即讓路曰:“迷魂鬼來了。”
一日,復見打雀子,狩夫正標射時,即拍掌念阿彌陀佛。狩夫見之,氣憤填胸:“你再不走,我就(摔-率+衰)![]() 你一銃!”我更不肯走。一見雀子彈死,即念《往生咒》饗之;見牛馬猪狗各畜類,用手撫而歎曰:“你何苦受此身形?幾時能脱驅殼?”動輒淚下不止。此十歲左右事也。
你一銃!”我更不肯走。一見雀子彈死,即念《往生咒》饗之;見牛馬猪狗各畜類,用手撫而歎曰:“你何苦受此身形?幾時能脱驅殼?”動輒淚下不止。此十歲左右事也。
至十二歲時,每念世態多幻,畢竟蓂茁蜉蝣,終非久住之地,立志出家。遂跋涉至漢陽,滿擬到歸元寺出家,因不知寺之住址,錯到歸元頂;一進見之,酒肉熏心,嘔吐掩鼻,望而知退。予忖度之,定非真歸元寺也,恨我因緣乖謬,造化所苦。正危念中,適堂兄忽來,拖走逼歸,致未遂出家之志;如是氣絶者數次。
一日,父令長跪棹前,邊靠一木棍,父拈肉一塊逼我吃,吃則罷休,不吃,三棍打死除害。我即禀父:“請父打死,誓不吃葷。”我母即攔住。
是年皈依大智老和尚,我問何法能了生死,彼僅教以念佛法門,且曰:“汝能念到睡著做夢還有佛聲,再告大法。”如是埋頭苦誦,晝夜忘疲,能一時做到夢中念佛,師再有大法可告,喜不自勝。
急不容緩之一句阿彌陀佛,不出聲念,易得忘失;出聲念佛,恐親不樂。行念有間,即用竹板,書“南無阿彌陀佛”六字挂在傘內,若忘念佛,竹板撞響即警覺,佛聲不斷;若坐,即將竹板放在懷內,忘則取出,視之即念。至睡時,每被夢轉,無法念佛,即用净水供佛前,至晚持水用食指畫“南無阿彌陀佛”數十遍吞下,使夢中念佛。諸法設盡,未得夢中歷歷明明念佛,心甚焦急。
一日,詣寺省師,至夜靜坐,睡夢中大聲念佛,驚醒師傅,特來問曰:“你大聲作麽?”喊不應,推方甦。
師問曰:“汝睡著念佛可知麽?”我答不知。
師曰:“此真誠念佛也。”
一聞師言,肅立欣慰,曰:“請師再告了生死大法,可乎?”
師即問:“念佛是那個?汝可知否?”我被這一問,如喝一口冷水,往下一吞,臉燒飛紅,半時不能答,冷坐若呆。
我復問曰:“此法如何用去?”
師云:“候你將念佛的這個人找出來,再向汝道。”師回寮休息,我內心煩躁,意頗躊躇,若學參毫無把握,若學念又覺困難。此十五歲時事也。
由是世塵之心冰冷,參禪之念益堅。時值父病彌篤,醫藥罔效,常思古人爲親盡孝,我何人也?即夜取菜刀,私入佛堂,虔誠拜禀諸佛,自願割肝救父;盟誓畢,復覓定磨刀石一塊,恐防不濟,結跏趺面佛而坐。至深夜自解上衣,正胸膛下,用刀力剖,數十轉未開,刀鈍復磨,再剖方開,刀無血迹,身未沾紅,內有乾血一團滚出,見之極圓,即用右手伸入,取肝一塊,割下三分之二,內如沸水之動蕩;割後刀口無法收閉,熱氣外冲,即將褲帶攔口捆緊,起身禮佛,取豆腐合煮熟透,親送父床喂食。食之還要,我即婉言安慰,侍父睡著,不多時病愈。此十八歲時事也。
父母逼我大婚,慈命難違,無法迴避,衹得事前與女商約:結婚時,名爲結褵,不染世緣,各行佛道。該女早已爲我化歸三寶,茹齋誦佛,豈知該女道心更為貞切,早有不落紅塵之志,反勸我終身為道是求。至期虚與同房三日,我坐蒲團,女坐椅杌,陪母閑談,母住房勸慰,定要我等安睡方出。如是者三日,母知世俗無緣,怏怏而去。我等各歸佛堂,修性念佛。此十九歲時事也。
至是父母、兄弟、妯娌悉勸回頭,吃齋念佛。我每夜佛堂領衆修行,除父不能盤膝外,其餘皆長夜不倒單者多年。
至二十二歲時,被叔祖父逼同到任年餘,因公牘中極刑過多,功微過重,目難忍睹,辭職歸里。雖在官場,佛珠尤未曾須臾離手,每日佛聲不斷。至閱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云:若人受諸苦惱,聞是觀世音菩薩名字,即時觀其音聲,即時解脱。靜思猛省,念“釋迦牟尼佛”數句,即時觀聽佛之音聲,其時身心清净,萬念潛銷;方知此事最尊最貴,最上第一,要辦此事,非出家不可,如是蓄意趕辦行裝。我見母親既已皈依三寶,兄弟、妯娌全家信佛,外有皈依者數百人,對於世間孝道禮義略盡少分。所憂者父親,雖逐漸信佛,尚未戒口,是我終身鬱悶遺憾事也。
由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一日,向雙親告假,朝谒南海,預到普陀出家。將登海岸,見僧人口含紙烟者、身穿綢褂者、手把洋傘者、腳穿白襪者,奇形異色,不一而足。當時心生冷落,急將用款在前後寺打齊供衆;作功德畢,即往梵音洞捨身。此捨身事,後文補叙。此時遇有五位穿衲襖、科頭赤腳苦行禪師,觌面相談,長歎曰:“還有真修行人在焉!”遂願出家。自即潛購剪刀一把,私往三聖堂南山麓,將發剪下,搓團置埋泥裏;又將鞋襪摔棄,先辦一件破袍子穿上,科頭赤腳,了盡我生平之願。五苦行比丘,偶一見面,即吐舌曰:“汝那裏落髮,何不與知?”該五人不離方寸。至六月二十五日,私自過海,擬行頭陀苦行,彼五人聞之,不忍獨去,遂一同過江。我不願彼等同路,求他給一方便鏟、棕蒲團、木瓢、筷子;瞞他,遂向深山奔躲。
離開後,竟絶食三日,在山打餓七九天,上下四天,共十三天未吃飲食;由此一餓,家情俗念,徹底忘清。出家後,自願往寶華山受戒,單瓢化食,擬趕華山。不料夜歇水邊,僧帽、瓢、筷、便鏟等物,被行船縴繩經過,齊颳下水,杳然無踪。
次日,覓一竹棍,化一瓦盆,一路求食,有五天未食者,有三天未見粒米者,日夜奔馳;將到寶華山邊,無力上山,又無衣單,即取青藤一條,將破衲襖綑好,當作衣單,平路背行,堵則扒(扒同爬)走。多天未食,氣力毫無,挨至客堂拜下,無力起身;該知客師未識來意,向臀股(摔-率+衰)![]() 起一腳,如是倒睡在地,無力起扒。知客大師,連吵帶吼,著照客扶起問:“戒費有否?”
起一腳,如是倒睡在地,無力起扒。知客大師,連吵帶吼,著照客扶起問:“戒費有否?”
答:“無。”
又問:“號條有否?”
答:“無。”
“衣單有否?”
答:“無。”
又問:“來做甚麽?”
答:“我來受戒的。”
知客哩納過,隨送一小房內。舉眼一看,門縫挂有草紙一張,請照客借一筆硯,即書云:“普陀離俗意欲奢,實爲生死到寶華;多蒙師衆收留我,參明本性脱塵沙。”貼內墙上,因苦到此地,感激之意。
隔二小時,有巡照師來房,先將字條看過,復將我頭細看一周。到客堂,隨來二知客,先看我頭,再看字條,問云:“你是新戒?是老戒?”我不知新戒、老戒爲何物,故未即答。又將我移住碾磨坊,知客見我頭上有幾個巴子,定是山下大馬溜子欲來打劫。“新戒那能説得這幾句話?你們大家留心謹防,定不是好人。”可憐我此時還未知這四句詩偈送命,又在碾坊墙上續題四句,曰:“寶藏重開透性天,華嚴海會度深泉;仙佛普利無邊際,山放光芒奠大千。”用“寶華仙山”四字為題;不半天,有知客見到,即囑碾磨頭與大衆云:“此人定非好人,請你們看看此四句,究是新戒能寫出來麽?”衆人加倍用白眼看我,遇笨重過穢事,直令我做。
我在家未倒單,出家也未倒單,與衆新戒同一床,我坐不睡者,月馀;點小燈防我者,亦月馀。
浩老問曰:“點燈作麽?”
碾磨頭云:“有個新戒是歹人,特點小燈防他,否則恐盜寺物。”
我又屙血七日夜,睡磨盤內多天,衹餘一息。同戒者教我溜單,我不知溜單是犯送命的規矩;次日早,將同戒幹飯吃飽,將衲襖依舊用藤一綑,負到肩上。碾磨頭問曰:“你做煞(煞同啥?)”我云:“溜單。”他云:“好。”可憐一跑直到黑鳥龜石,碾磨頭追來,帶一茨條,棍身死打一頓,提耳拖回,如拖猪似,直到巡照樓上跪下,巡照云:“琉璃燈扯起,毛竹板子打斷。”氣絶者數分鍾,莊主討保始饒。二人扶回原處,坐下細想,方知溜單一事,不許人知。
雖規矩之嚴,執事之緊,誠利天下、範後人。思之,我若不是幸遇各大善知識,刻骨究實提拔,我何能爲高旻一代住持?粉骨碎身,難報萬一。誠律宗戒法之嚴、消業之深,為成佛之基本,作菩薩之種子也。
即至次日,衲襖不要,早飯不吃,私自逃出後門。走四五里,猛從深柴山窠直進,又恐捉住,下山至稻田中行,看稻者擬開铳驚駭,我落荒不能走;黑夜向彼要求下山苦衷,後放我走。徑來金山求住,預為受戒,我話未畢,知客派衆僧,連推帶拖,一擁而出,云我是馬溜子。兩三天未吃,求一餐飯亦不准;他云:“空手不能趕齋。”該小价拖我離開山門。可憐日暮途窮,渺無去向,衲襖丟在華山,身衹穿一道士與我單藍褂,直至鎮江街心,沿門討飯,人見我身無衣穿、手無碗筷,無一與之。如是三天,竟未得一粒米。偶遇一道士,我即扯住跪下,哀求曰:“我做和尚遭難,現在情願做道士。”
該道士云:“我廟在棋盤山頂,你去云是當家叫來的,不久即回。”
我聞急上該山,等侯四點鐘,該廟當家,亦出外回,將我一看,即著人趕快拖出去,定是壞人;即時來五六道士,將我連拖帶抬,向柴堆邊一(打-丁+衰)![]() ,驚動群狗,騷然狂吠,我即佔住狗窠一夜,五六道士巡查。
,驚動群狗,騷然狂吠,我即佔住狗窠一夜,五六道士巡查。
至次日,眼睛皆黑,到下晚方明。下山復到金山塔院七里甸,跪在當家前求救亦不准。是時正開山洞鐵路,我擬傭工挑土,苟廷性命,再好尋師受戒,即向該處逐一詢問,扁擔、糞箕須要自備,方准入場。思之,一文未有,那有錢置物?至是討飯無人給,做和尚無人收、做道士無入要、做工又無本錢,直到山窮水盡,就在去七里甸十里許小土地廟內,與化子同歇一夜。
至次早立誓云:“此處動腳,直抵大江,無人救我出家,自願投江而死,轉世再來。”如是走一腳,滴一淚;思之,命在這條路上,達到江頭即死。問人大江距此多遠?得有人指迷曰:“還有八十里,即揚子大江。”嗚呼!死之時間,當在頃刻。八十里地中,見僧人即跪下求救。至離鎮江四十里,有一小廟,進廟跪下求食,他云:“食飯現成,你到田上,拔黄豆稭一擔,挑回再吃。”即時去扯挑回。當家外出,女眷不能當家,他們吃白飯,我在一邊冷看。可憐豆子挑回當家他處,不料竟餓一天一夜。
次早,當家令我他去,起身又跑到彌陀寺;地方甚小,當家甚善,我求即允。他問我:“你還有力否?”我答:“能挑五百觔力。”“你能看山否?”答:“能看山。”
至晚,燒五人稀飯,被我一人吃空。工人回時,坐歎冷氣,有恨當家不該留我者,有怒小价不該多添飯者,鬧得當家不安。當家次晨,找破爛衣服一包,囑我到句容縣寶塔寺討單住下。再想此位當家,正是我救命恩人,即時飛跑,即到寶塔寺,老當家留當行堂。
回顧前之立誓,若無彌陀寺救星,直抵大江,必置身水葬。思之,由發心朝海,披缁至此,雖不若善財之百城烟水,亦有磨身捨命,為道是尊。稍似彷彿,聊衹依稀,實際研塵刮垢,去習銷愆,有不可思議之受用。此二十四歲時事也。
受行堂執後,身體強壯,道念更堅,從此重立大誓;盡此形壽,任死再不動筆作文作詩。回思華山事,皆由文字構害一致如此,今而後,做一粥飯僧人,蓬願足矣。二時,隨衆上殿過堂,動靜不離“念佛是誰”工夫。
自思:前之所行,磨煉身心,掃除惡習。一向愛身如寶,衛生若勤,徹底放下,渾不顧及,依法出家,求師受戒,否則將成庸輩。輒有人問我曰:“汝有師否?”
對曰:“未有。”
他云:“我可成就汝,好吧?”
對曰:“很好。”可憐舉目一看,無人能為我師者。認定閑居一位老修行,燃指拜佛,禪宗多年,四名山、八小山朝過,似有道貌。一日往寮請示,進門一陣青煙衝出,我疑佛香;三拜畢,請師賜一號條,往金山受戒,師即取名。我辭出寮時,囑師云:“師傅多年苦行,被一黄烟熏下地獄,徒心不忍。”師云:“向後決定不吃。”
過數日,復去探查,師見我進門,急將烟具藏好,我各處尋覓,找出黄烟杆一根,隨折兩斷,從窗縫丟出;黄烟一包,携出放散園田。又囑云:“師若再吃,今生不來師前問安。”説畢,號條收取,又找衲襖、方便鏟、僧笠子、瓤囊一齊辦好,先到茅山朝陽洞。打一餓七畢,出外問人:“今天幾時?”
彼答云:“今天是二月三十日。”
猛然懊喪云:“不好了,金山戒期又趕不上。”如是晝夜飛跑,至初二日趕到金山客堂,將方便鏟、蒲團放好,衲襖科頭赤腳,進客堂問訊坐下。知客出,行禮如儀,問云:“老修行那裏行腳來?”
我云:“師父慈悲,弟子來山求懺悔的。”此受戒的話,在寶塔寺學會的。
知客把臉一變云:“我看你像老參的樣子,原來是個新戒。”
知客先是必恭必敬,當行頭陀苦行的老參挂單,後知新戒,隨與挂號;問戒費,我云:“没有。”
知客云:“既受戒,何以不帶戒費?”即用楊枝條杖我五十幾下。
衆師承有助戒費者、有助衣具者、有助被單者,戒費、衣單齊備,送堂隨衆還未忘“念佛是誰”工夫。一到戒堂,見“念佛是誰”四字,即放衣單,向四字磕四響頭。咦!這裏也有“念佛是誰”,喜不自勝。金山是禪堂,做新戒堂故也,凡散來遮難文各件,目兩遍即能熟背,坐如呆子似。
至戒期圓滿,各人四散,獨我一人無他去向,就勉強在學戒堂住。他人學唱念功課,我無事,即將“念佛是誰”作一整篇文章,貼房內自賞玩之。忽維那見到,急催進堂;不三閱月,首座每天舉罰,云:“這位新戒道心很好,白天吃一餐,夜裏不倒單;破壞清規,下次不准。”我思之:挨香板可以,破壞清規不可以。由是發心出外吃鉢飯,准備直抵中印度,終身覲佛道揚,死而後已。適有老戒,名“雲先”者,定要與我一同行腳,拒之再四,誓與我同生死,無法離開。
一路至江北數十裏,飢時擬用鉢化飯。請他前行,一村狗子攢吠他,無法抵禦;我復前行,狗趕後咬他,彼即大生退心,云:“我恐不及,請你一人先去。”如是“一鉢千家飯,孤身萬里遊;欲問前途路,究竟是誰走”?從此立行,每日太陽將出,先舉“念佛是誰”起身,手拗蒲團,舉工夫上肩;至晚,太陽將落,即放蒲團為止,或止在橋邊、路邊、屋邊、溝邊、山邊、水邊、墳邊、糞邊,概我止處。但先提工夫,後放蒲團,若一次空放者,即提起重舉工夫再放,日爲常課。誓不挂單、不趕齋、不歇店、不化緣、不倒單、不問路、不洗澡、不存一切,如願而行,未稍違犯。一路經過事實,容後再敘。
行至五臺,見一白塔,即禮拜,知是文殊塔,不謀而到;朝五臺後,即向北由桂花城出國,擬往中天竺。一路盡是葷食,別無素食可餐,故不能吃;見每樹下爛棗纍纍,撿食一飽,以充其飢。忽有東印度來中國進香之喇嘛,向我問訊,彼此談話,他云:“來中國三年,欲回本土,因途中障礙太多,不敢妄行,特回中國。”我聞之通身冰冷,即時共辭而別,返回中國。
適值隆冬,大雪三尺多深,前不知路,後無烟村。在深雪中過一夜,身寒冰透,身穿衲襖,重十五觔,每下雪雨三五天,堅坐三五日,蒲團下,坐成窠塘,水浸半身,其衣加重十馀觔,身幸未傷。一路與告(告應為叫)化子同睡者、與狗子同夜者,回數很多。
自思:既不能往印度,衹好回里,化父皈佛。主意既定,隻身飛跑,直到本鄉,擬上家廟住宿,次日再行化導。不料,將進廟門,適父同進廟內,隨即禮父三拜。父云:“母眼哭瞎,父找汝,朝山四五處。”父即將我蒲團拗歸本家。
小弟見曰:“父將這邋遢和尚弄到家來作麽?”父即云:“是汝二哥到家。”衆鄉鄰親屬悲喜交集。隨時令衆親屬人等,排班整齊,開導云:“浮世非堅,趕急回頭,皈心三寶。”勸畢,令各散去。
即請父出外上坐,大勸一番,父之哭聲震耳,我亦同哭。父云:“你要我皈依三寶,我要皈依你,皈依後不能遠遊。”我隨口答應。父皈依畢,即告修行路途,隨時向雙親告辭而別,直抵金山銷禪堂假。此光緒三十三年春間事也。